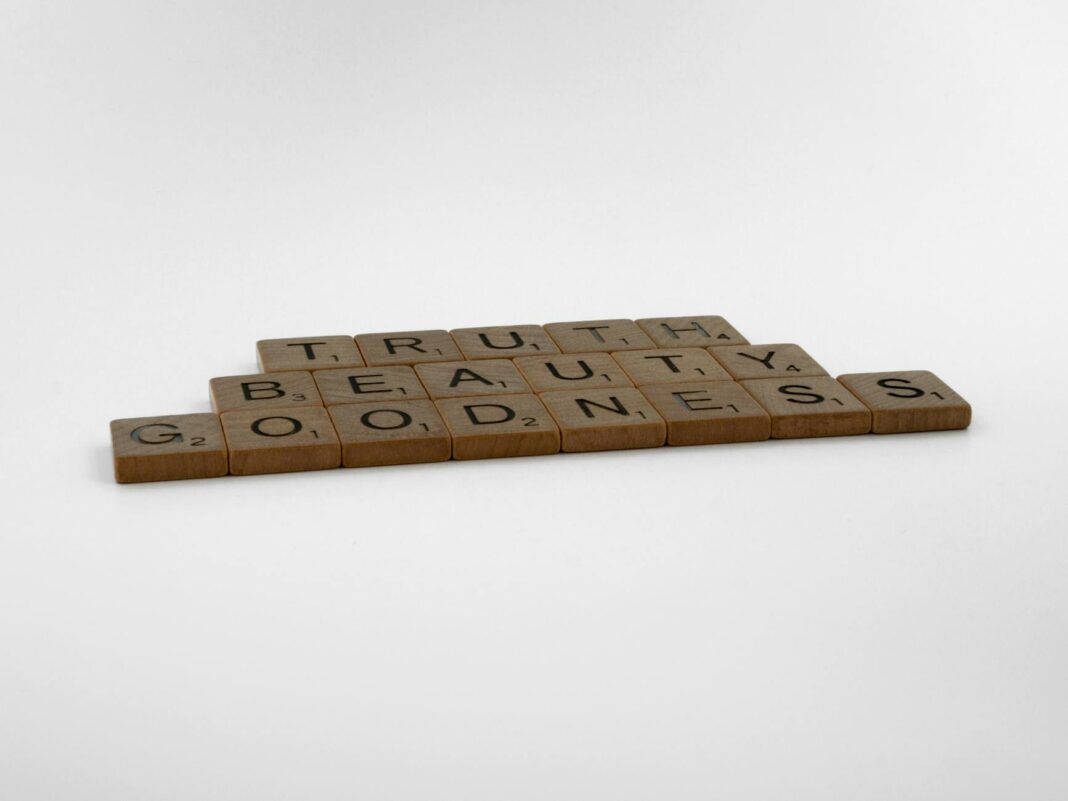——从诺贝尔经济学奖“制度与繁荣”视角分析政治体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结
一、引言:繁荣与衰败的真正界线,是制度的善与恶
历史上,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追求“富强”的目标;
但有的国家繁荣长久,有的则盛极而衰。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·阿西莫格鲁(Daron Acemoglu)在《制度与繁荣》(Institutions and Prosperity)演讲中指出:
“社会的繁荣,不取决于地理、文化或资源,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——制度塑造激励,而激励塑造命运。”
制度不仅是一组规则,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伦理。
若制度的设计以保障自由、约束权力、维护法治为目的,它是“善的制度”;
若制度的运作以剥削、控制与维护统治为目的,它就是“恶的制度”。
当代学界往往把政治体制分为“民主”“独裁”“威权”等类型,但这些概念多是形式上的。
真正的区分,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,而在于权力是否受制于法、是否服务于公共利益。
这种善恶之分,比民主与独裁的名义划分更能揭示现实。
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虽有选票制度,却同样陷入腐败与贫困;
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威权体制能在短期内动员资源,却必然走向枯竭。
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与终结,正是这场“善制与恶制”循环的典型案例。
二、善的制度与恶的制度:政治哲学与经济伦理的双重维度
(一)善制的本质:权力约束与自由保障
“善的制度”(Good Institutions)不只是经济规则的优化,而是一整套政治伦理结构。
其核心原则是:权力被制度所限制,个人被法律所保护。
其主要特征包括:
- 权力分立与制衡(Checks and Balances)
任何权力必须受到法律与公众的监督。
政治制度的正义性来自其自我约束能力,而非权力者的“德性”。 - 法治高于人治(Rule of Law)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统治者也受其约束。
这是善制区别于恶制的最清晰标志。 - 基本自由与社会信任(Freedom and Trust)
言论、思想、结社和经济活动的自由是社会活力的来源。
当人民无需恐惧地表达意愿时,社会才能形成自我纠错与创新能力。 - 公共权力的服务性(Service Orientation of Power)
政府存在的目的,是保障公民权利与公平竞争,而非实现统治集团利益。
这种制度不是抽象的理想,而是历史上真正导致繁荣的政治现实:
从英国的宪政革命,到美国的宪法体系,再到北欧的社会民主政体,无一不是通过权力约束与法治共识实现了社会富裕。
(二)恶制的本质:权力垄断与社会掠夺
与之相对的“恶的制度”(Evil Institutions),表面上可能高效、统一、强力,实质上以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为目标。
其典型特征包括:
- 权力无制约:
政治体制缺乏监督机制,权力集中于个人或集团。 - 法治被替代为政治意志:
法律成为统治的工具,而非约束的框架。 - 社会资源被垄断:
政治权贵通过国企、金融与行政系统控制财富分配。 - 思想被单一化:
宣传体系主导公共舆论,批判性思维被压制。
在这种体制下,经济政策可能表面理性、实质反人性;短期增长掩盖长期腐烂。
苏联的崩溃、委内瑞拉的崩坏、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,都是恶制运作的极端后果。
三、改革开放的“善制时刻”:政治松动与经济解放(1978–2008)
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,是善制逻辑的一次意外闪光。
虽然政治体制仍是单一政党,但经济与社会层面发生了局部制度善化:
——权力暂时退后,社会获得空间。
(1)政治权力的局部退场
在邓小平的务实主义下,政治意识形态被部分搁置。
地方试验被容许、个人创业被容忍、外资被引入。
这种“让社会试错”的政策,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谦抑——
政治承认自己不能决定一切。
(2)法治与契约意识的萌芽
随着市场机制恢复,法制建设被提出。
《民法通则》《公司法》《合同法》建立了基本的产权保护。
即便这些法律仍受政治限制,但其象征意义巨大:
它标志着经济关系开始摆脱政治命令的完全统治。
(3)社会信任与民间活力
80–9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混乱,却充满创造力。
个体户、乡镇企业、外贸商人、科技创新者——他们共同构成了“草根资本主义”的浪潮。
这是制度善化最直接的表现:人们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。
(4)外部开放与国际规则融合
加入WTO(2001年)之后,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。
知识产权、贸易法、金融监管逐渐与世界接轨。
这一时期的增长,是善制精神的成果:
政治虽未民主化,但权力对社会经济暂时保持克制。
四、恶制的回潮:政治再集中与社会封闭(2008–2025)
(1)危机后的制度反转
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中国体制的分水岭。
以“国家安全”“稳定”为名,政治权力重新扩张。
4万亿投资计划、国企回潮、金融垄断、土地财政的泛滥,使社会重归“行政动员型经济”。
(2)权力再集中与“政治至上”
2012年之后,制度的逆转达到顶峰。
反腐运动在清除腐败的同时,也清除了制度竞争与权力制衡。
党政合一、思想统一、社会监管技术化,使权力重新成为唯一的资源中心。
(3)私有产权与自由的退化
从“共同富裕”到“反垄断整顿”,私企和民营资本成为政治调整的对象。
经济政策不再以效率为导向,而以政治忠诚为标准。
企业家的合法性取决于政治表态,金融监管取代市场竞争。
(4)思想控制与社会冷漠
恶制不仅压制经济自由,更窒息思想自由。
教育、出版、网络舆论全面回到政治意识形态框架。
批判性知识被排斥,社会讨论退化为口号化。
这意味着善制时期短暂出现的“自由空间”彻底关闭。
从经济到文化,中国重新进入一种制度封闭循环:
权力—控制—掠夺—危机—再控制。
五、政治制度的共生规律:权力如何决定经济命运
诺斯(Douglass North)和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都指出:
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性质。
经济规则只是政治结构的外延。
当政治制度是开放的,经济自然趋向包容与竞争;
当政治制度是封闭的,经济终将成为权力工具。
因此,经济自由无法在政治专制下长久存在。
中国的改革开放曾试图“经济开放、政治封闭”并行,但这种双轨体制注定短暂。
权力中心化的惯性最终吞噬了市场自由。
恶制的生命力强于善制,因为它能通过恐惧维持表面稳定;
但善制的生命更长,因为它建立在信任与自发秩序之上。
六、善恶制度的文明后果
(1)善制社会的伦理逻辑
善制并非完美无缺,却具有自我修复能力。
因为它容许批评、尊重多元、承认错误。
这使社会可以在犯错后重新平衡——如美国的金融危机、欧洲的债务危机,都未动摇制度根基。
(2)恶制社会的必然崩坏
恶制的稳定来自压制,崩溃来自真相。
当权力不受约束,社会信任消失、信息被封锁、创新停滞。
短期繁荣掩盖不了长期僵化:
苏联的工业神话最终瓦解于官僚主义;
当代中国的科技梦,也在体制约束下陷入政治表演。
(3)制度伦理的核心:人是目的而非手段
康德说:“人永远是目的,而非手段。”
这句话是判断制度善恶的哲学底线。
一个以人权、自由与尊严为中心的政治体制,无论形式为何,皆属善制;
一个以统治、控制与服从为中心的体制,无论口号多宏伟,皆属恶制。
七、从中国的制度循环看未来
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验,是善制与恶制交替的历史:
- 1978–2008:政治松动 → 经济自由 → 社会繁荣
- 2008–2025:政治收紧 → 经济萎缩 → 社会焦虑
这种循环的根源在于:政治体制始终未能建立对权力的制度约束机制。
改革开放的成果建立在权力容忍之上,而非法律保障之上;
当容忍消失,一切成果皆化为乌有。
若未来中国仍停留在“强力治理”与“意识形态安全”的思维模式中,
经济复苏将只是幻影,社会信任将继续流失。
唯有真正重建法治、确立权力制衡、保障公民自由,
善制才能再次萌芽。
八、制度的善恶之辨:超越“民主—独裁”二分法
传统政治学研究中,制度往往被二元化为“民主”与“独裁”或“威权”,但这种划分在解释现实政治经济结构时显得过于表层。许多国家名义上实行选举制度,却依然陷入腐败、贫困与权力固化;反之,也存在在某些历史阶段通过善意威权实现制度性转型的例子。
真正区分制度性质的关键,不在于形式上的权力来源,而在于其内在的善恶结构。
从阿西莫格鲁的“包容—汲取”框架出发,我们可以重新定义:
- 善的政治制度(benevol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):
其核心是约束权力、防止权力垄断、保障个体尊严与参与权。善的制度以“公共善”为导向,通过制度化的问责与法治机制,使统治者成为社会契约的执行者,而非社会资源的掠夺者。 - 恶的政治制度(maligna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):
其本质是将权力神化、个人化或集团化,把国家机器变为掠夺工具。恶的制度通过意识形态垄断、暴力威慑与信息控制,将社会财富与政治安全转化为统治集团的私产。
因此,政治制度的善恶,不在于它是否“民主”,而在于它是否以人为本、以权受限、以法为上。
九、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同构关系
阿西莫格鲁在其演讲中指出:
“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形态,而经济制度的分配结果反过来强化政治制度的稳定。”
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繁荣或衰败,不是由经济政策本身造成的,而是由背后的政治制度逻辑决定的。
善的政治制度自然孕育出善的经济制度;恶的政治制度则必然塑造出掠夺性经济结构。
我们可以用“制度同构性”模型来描述这种关系:
| 政治制度 | 经济制度 | 制度特征 | 长期结果 |
|---|---|---|---|
| 善制(权力受限、法治、公平) | 包容性市场制度 | 创新激励、产权稳定、社会信任 | 持续繁荣 |
| 恶制(权力垄断、意识形态控制) | 汲取性经济制度 | 权力垄断、寻租腐败、创新冻结 | 衰败与危机 |
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演变中,这种同构关系表现得极为清晰。
1978—2008年间,政治相对分权、政策实验空间大,经济制度得以在局部地区形成包容性机制;
而2008年之后,政治权力重新集中、监督与法治退化,经济制度随之“恶制化”,形成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回潮。
十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底层逻辑
(一)“有限善制”的阶段性成功
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建立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上,而是源自一次“务实松绑”与“政治妥协”。
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逻辑可以概括为:“政治上不动、经济上放活。”
这种模式虽不符合西方意义的善制,但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窗口——权力被暂时分散、市场被局部开放、法治部分建立。
其成果是显而易见的:
- 地方竞争带来了政策创新(如深圳特区实验)。
- 法治雏形确立了企业家的信任基础。
- 政治高层“韬光养晦”的战略使外资进入与全球合作得以扩展。
这是一种“过渡性善制”,虽非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民主,但因权力制衡相对分散、法治尚存空间,故能支撑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。
(二)“恶制回潮”的结构必然性
然而,善制若无政治制度的根本保障,终将滑向恶制。
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,中国政治权力的重新集中与意识形态的强化,标志着这一过渡期的结束。
几个关键转折点说明了这种逆转:
- 党对经济全面领导的制度化——企业、大学、媒体等全部被纳入政治控制体系。
- 法治退化为人治——法院、检察系统再度政治化,司法独立性丧失。
- 意识形态压制——社会讨论空间被收紧,信息自由受限,创新环境恶化。
- 国家资本主义复归——“国进民退”成为常态,民营经济被政治风险所笼罩。
这些变化表明,恶的政治制度必然诱发恶的经济制度:
当权力缺乏制约,市场就不再以竞争与效率为准绳,而以忠诚与服从为生存条件。
十一、善恶制度的循环: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困境
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显示,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都经历了“善制兴起—恶制腐化—再生改革”的周期。
这一规律可见于古罗马共和国的衰亡、清代康乾盛世后的专制化、以及苏联从革命理想到极权的演化。
中国的现状,正处于这样一个循环的“逆转阶段”:
- 改革开放的制度成果正在被恶制吸收;
- 政治合法性重新依赖控制与恐惧;
- 社会创造力与信任正被系统性掏空。
阿西莫格鲁的理论提醒我们:制度的退化并非自然现象,而是政治意志的产物。
当统治集团把维护权力置于公共福祉之上,制度便从善转恶。
十二、从苏联到中国:恶制的自我强化机制
苏联的历史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镜像。
苏联在1950年代后形成了典型的“汲取性制度”:
- 政治权力集中于党;
- 经济计划抹杀市场信号;
- 知识与思想受意识形态审查。
尽管苏联在工业化阶段实现了高速增长,但长期停滞不可避免。
中国今天的制度路径与苏联晚期高度相似:
- 政治结构拒绝改革;
- 技术创新依赖国家计划与补贴;
- 外部开放被安全逻辑替代。
恶的制度拥有强烈的自我强化机制。它通过“忠诚筛选”消灭异议者,通过“政策依附”维系内部特权阶层。
最终,这种制度的“稳定”恰恰是停滞的前奏。
十三、善制的条件:法治、自由与责任
若要避免恶制的自毁循环,一个社会必须重新确立三个原则:
- 法治高于政治
- 法律必须独立于权力意志,成为限制统治者的工具,而非镇压民众的武器。
- 经济自由与产权保障
- 任何创造与投资活动都应免于政治任意干预。
- 国家应保障市场竞争,而非充当最大利益相关者。
- 政治问责与公共参与
- 政治权力应受到多元监督,包括社会组织、媒体与司法体系。
- 当社会有渠道纠错,制度才具备长期生命力。
善的制度之所以可持续,不在于它完美,而在于它允许自我修正。
恶的制度之所以必亡,是因为它拒绝纠错,只能通过暴力维系秩序。
十四、中国的前景:从“繁荣假象”到“制度危机”
中国当下的经济放缓、失业上升与资本外逃,表面上是周期性经济问题,实质上是制度退化的结果。
- 当创新被政治控制替代,科技便成为宣传;
- 当企业家被威慑而非激励,投资便转向逃离;
- 当权力压倒法律,社会信任即告崩溃。
正如阿西莫格鲁在诺贝尔演讲中所言:
“当权力不能被问责时,社会的繁荣必然会终结。”
因此,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结,并非政策失误,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局。
一个制度若从包容走向掠夺,从开放走向封闭,从法治走向人治,繁荣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。
十五、结语:制度的道德维度
经济学长期以来被视为“价值中立”的科学,但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揭示:制度的善恶具有道德意义。
制度不是冷冰冰的规则集合,而是社会如何对待人的方式。
善的制度尊重人的尊严、保护人的自由;
恶的制度利用人、恐吓人、牺牲人。
改革开放的真正遗产,不应是GDP数字,而是那段人们敢于尝试、表达与创造的时代精神。
若这一精神被制度扼杀,则所谓的“发展”只剩空壳。
正如哈耶克所警告的那样:
“通往奴役之路,往往始于对秩序的迷恋与对自由的恐惧。”
制度的善恶,不仅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,更决定其文明的方向。
唯有重新建立一个以法治、公平与自由为核心的善制体系,中国才能重新获得真正意义上的“繁荣”。
参考文献
- Acemoglu, D., & Robinson, J. (2012). Why Nations Fail: The Origins of Power, Prosperity, and Poverty. Crown Business.
- Acemoglu, D. (2019). Institutions and Prosperity: Nobel Lecture. Nobel Foundation.
- North, D. C. (1990). Institutions,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Hayek, F. A. (1944). The Road to Serfdom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Olson, M. (1982).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. Yale University Press.
- 罗宾逊,《包容性与掠夺性制度的政治经济学》,哈佛大学讲座,2018。
- 中国统计年鉴(1978–2022),国家统计局。
- 世界银行,《治理指标报告》(2010–2024)。